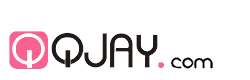上海一连下了一个星期的雨,在南京办完分享会过来的Blake跟我说,南京也是大雨不断。
整个长三角都在下雨,每个人都多少皱些眉,我想广州的艳阳天了。
不过也有好处,下雨天是很适合看电影的。
当代文学课在晚上,雨夜,没想到老师真的放了电影。窗外漆黑一片,大家屏息看着,投影布上的光映在每个人脸上,窗外的雨声听得清楚,比电影院里浪漫得多。
电影是《小毕的故事》,80年代的金马奖最佳剧情片。三十年前,只有17岁的钮承泽演男主角,完全不能想象那个到处开黄腔的《艋舺》导演,竟然也曾有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。
国中生小毕从小就和妈妈以及继父生活在一起,一直喊继父“爸爸”。小毕一向叛逆,常常打架,最后捅伤了同学,向来包容的继父气得发抖,第一次说了狠话:“我不是你爸爸,我没那么好命。”
小毕听了倒不难过,但温柔的妈妈愣住了,没说话。第二天,妈妈照常为小毕准备好便当,将家里打扫干净。
做完这一切,她却开了瓦斯自杀。
影片里的故事还有很多,80年代的台湾生活、美丽又和淡的海岛风景、善良美好的人情等等。不过,小毕妈妈的自杀显然是故事里让人难以释怀的部分,她太过软弱,对恶言几乎毫无抵抗能力。
其实这样的故事很多,也许并不那么极端,但总有些人,因为一句话说岔了,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退出的过程不是短暂、缓慢如地壳运动,而是迅速的、剧烈的,像地震那样。
小茉莉去了那个必须随身带伞的、多雨的国家。
给我打电话时,她那里、我这里都下着雨。她坐在窗边,慢慢吃一块披萨,告诉我她和那个曾经很亲密的男孩之间,现在隔了片撒哈拉。
男生和女生之间,最常出现的认知差异表现在微信上。男孩不太爱聊微信,一忙起来更觉得回女朋友信息这件事是个累赘,于是他吼小茉莉:“拜托你,就当放我一条生路,别再给我发信息了!”
原来我对他来说已经是项严重的扰民工程了。小茉莉苦笑,纵然这句话把她炸成内伤,她还是愿意“放他一条生路”。
这句话,犹如一颗投出的原子弹,此后就算再怎么道歉也于事无补。小茉莉再也没有回过他的信息。
有时候,把一个人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赶走,甚至不需要一句话,一个表情和动作就足够了。
我从小就不会唱歌,不是客套的不会,是真正的、一开口音调就离开地球表面的那种“不会”。但玉子唱歌很好听,她深知我唱歌跑调,音乐考试时,她总是很讲义气的跟我一组。
我们的音乐组合是不用排练的,因为她不用练就唱得自带共鸣,清泉流水。我也不用练,因为练了也白练。
到最后考试时,老师皱着眉侧耳在我两之间听来听去,下了结论:“你们的水平不适合一起唱,下次不要一起了。”只是下学期期末,我们又一起站到了老师面前。
在玉子的捆绑式销售策略下,我初中三年没唱对一个调,音乐成绩却一直是“优秀”。我和玉子是千千万万中学生好朋友里普普通通的一对,一起吃饭回家上厕所,每天互相交换学校里好看的男孩子们的最新消息,总以为自己时尚时尚最时尚,别人都是土包子。
初三快毕业时,老师把前几年的成绩单汇总发下来,几个女生围在一起看。她们对我三年来所有科目都全优的成绩感动惊奇,说了些赞美的话。
玉子在旁边听了突然“噗”一声笑了:“让她唱句歌听,你们就知道她怎么拿全优的了,他们这些优等生都是有妙招的……”同学们听了立刻用有一种充满怀疑的眼光看着我,好像我的成绩都是用一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得来的。
当时我不知道该怎样辩解,而事后呢,我则开始了和玉子的冷战。我既伤心又生气:作为好朋友,她为什么要这样让我难堪?她以为她帮我拿了音乐课的优秀就有资格这么说我了吗?
其实现在想来,那时玉子也许根本没有恶意,只是开了个欠妥的玩笑,或者单纯地想要申明这份成绩里也有自己的功劳,得到同学们的夸奖。
但是那时的我并未理解。玉子想结束冷战,对我露出八颗牙的、牙膏广告那样的笑,我从作业中抬头看她,她张口想说话,我冷冷地瞟了她一眼,又迅速低下头去写作业。玉子的笑容僵住,极慢地离开了。
从那以后,我们再没有说过一句话。
多年以后,我偶然得知那时因为我们的冷战,玉子常常躲在家里哭。
少年时不觉得一段让人温暖的关系有多珍贵,总以为人生才刚刚开始呢,这样的感情还会有,这样的人还能遇见。
为一个无聊的对错互不让步,一定要朋友们先低头才心满意足;为一点小事生气地说分手,一定要看到对方深深忏悔才肯罢休。
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先承认错误,还不是因为他们爱我,而我之所以可以用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就轻易地伤害到他们,还不是因为我们太过亲密,以致对对方身上的痛处和软肋了如指掌。
我们从陌生人开始,一步步了解对方,是为了建立一段美好的、给人以想象的关系,而不是为了气急败坏时,口不择言地说出一句把他们炸成内伤的恶言。
关系是这样的,在温馨的时刻,你看它,会觉得它很长很长,看不到终点,想当然地认为爱人们永远不会离开,这段感情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,因此吵一场架,冷战一段好像都可以被原谅。
但其实不是的,它随时有可能戛然而止,只是在你说出那句致命的话时,你没有听到心碎的结束音罢了。
今年六月毕业的时候,WhatYouNeed给我办了一个欢送会,但在那个party上,我并没有多欢乐,酒只喝了一点点,眼睛却哭得通红。
过去几年里,我和编辑们常常因为一篇文章发不发,甚至文章里的一句话要不要改进行激烈的争论,有时他们不听我的意见,我就生气,和Blake冷战,跟Jame大吵。
但直到要走的那一天,我突然很心疼那些被我浪费在冷战和大吵上的时间,原来我们能够相处的时间是那么短暂,能够一起经历的事情只是人生大海中的一粟。
一年的友情、两年的恋情,当时你以为很长很长,其实回过头看才知道它的短暂和脆弱,没有多少可以被我们浪费和消耗。
又过了很多年后,有着一个日式名字的玉子真的去了日本。我们辗转加了微信,却成了连朋友圈都不会互相点赞的关系。
而如今,每当我处于被大家怂恿唱歌的困窘之中时,想起的,还是只有玉子。